“长长的拒绝”[1]
——《柏慧》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马兵
《柏慧》是继《古船》和《九月寓言》之后张炜发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先是作为“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的一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推出单行本,转过年又刊发于《收获》1995年第2期。相比于两部长篇前作,《柏慧》的经典性和影响力似乎都要弱一些,一个直观的参照是,三年前同样发表于《收获》的《九月寓言》,先后荣获“上海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大奖一等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1990年代末又入选《文汇报》等所评“90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的榜单。不过,《柏慧》在张炜的创作中有着特别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长篇是张炜投到其时思想界的一份宣言书,与他同期的一系列散文如《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抵抗的习惯》《忧愤的归途》等一起构成他对深刻影响了新时期文学进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种回应。这场大讨论之中,作为“二张”之一的他一直处于讨论的风口浪尖,《柏慧》更是因为触及大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地位、责任及精神状态,与一系列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引发了始料不及的争执”[2]。就像有批评者在1995年的一个对谈中谈到的,《柏慧》“在90年代特有的精神背景下问世,它鲜明的‘融入野地’的精神倾向,它所引发的争议,说明它的意义已越出文学领地,成为当下一种突出的文学标本,深入讨论它,很有必要”,而且讨论的方式应是“借作品谈当下精神境况,借当下精神境况谈作品”[3]。我们今日重勘这部现象级的作品,依然要返回其时的思想语境,从作品“超小说”的文体入手,考辨张炜自1980年代而来的“长长的拒绝”如何塑造《柏慧》,进而探讨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它与1990年代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浪漫主义、民间话语,以及新时期其他文学潮流错位对话等的多重关系,以期在时人的判断之外,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 一气呵成”的“超小说”
《九月寓言》之后,张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家族》的创作准备中,这部后来成为大河小说《你在高原》一部分的长篇却在1994年春完成初稿后,“经历了一个大的停顿”,“因为我不得不放下它。我开始写《柏慧》……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在良知的催逼下,人该留下他珍贵的声音。是的,这就是我又一次中断《家族》写作的原因。我实际上走出了所谓的学术和艺术,直接面对一片目光一片耳廓。我并不指望那些人会理解我,它——《柏慧》,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声音”。张炜说,通常他创作长篇总会经历一个写作、搁置、与朋友讨论进而反复修改的过程,“唯有《柏慧》是一气呵成”[4]。张炜的一位友人提供了旁证,“那是1994年的6月—7月,正值暑期。我每次去他那里总是看到他在伏案疾书,后背渗出大片汗渍。他有时坐累了就蹲在椅子上继续写。当时我真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如此高的写作强度,然而他硬是顶了下来。这部书就是《柏慧》……”[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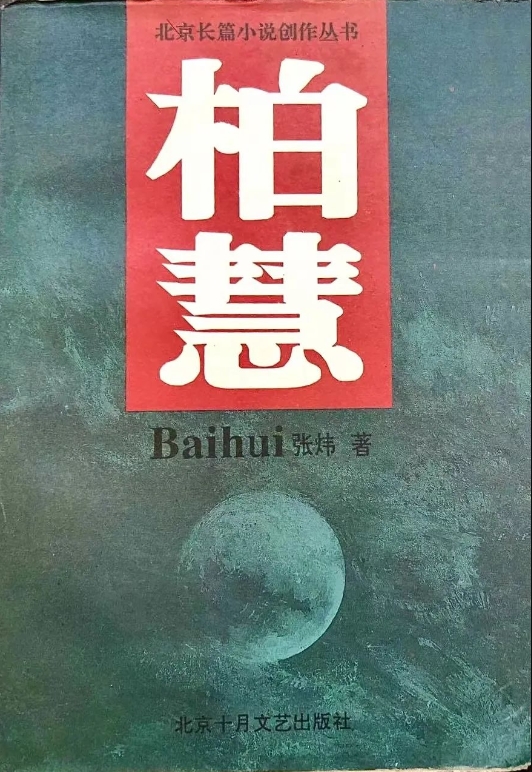
张炜:《柏慧》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虽然张炜声称《柏慧》不过是个人的声音,但他发声的时间节点,以及特殊的发声方式迅即在思想界激起波澜。这部“一气呵成”之作引发的争议之一是到底该如何理解小说所用的“倾诉—独白”体。就文本来看,《柏慧》由叙事者写给昔日恋人柏慧和恩师老胡师的三封长信构成,在信中他追忆家族经历和自己的成长,着重倾吐他从城市回到海滨故土的心路历程,也描述了在资本市场的虎视眈眈之下,他所坚守的葡萄园面临的重重危机。由于采用了书信体的形式,叙事者的主体性充分外显,通篇洋溢着坚贞的拒绝“滔滔的时代河流”的意志,他的倾诉中夹杂着大段大段的抒情、议论和判断,让小说如传道书般成为关于“我的立场”这个“最普通最基本的问题”的坦诚和愤激的表达。
孙绍振认为:“《柏慧》是用大人生随笔的方式写成的,其中没有完整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它所要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感怀。也就是说,支撑《柏慧》的是作者的思想记录,而不是作者体验世界而有的丰富的感性表达。”为此,孙绍振甚至指责《柏慧》是“不成立的写作”[6]。有意味的是,捍卫张炜的批评家同样认为《柏慧》是“思想随笔”,在本质上是“超小说”或“非小说”的,但却从正面肯定它是“一部为我们病态的文化时代和生存灵魂号脉的杰出的精神文本和文化文本,它是对我们溃败的世纪末文化的严厉诘问和最深刻馈赠”[7]。对于小说中间杂的大篇幅的议论和说教,有批评者赞扬其背后深沉的诗性力量,认为正是这“纯洁、峻急的情感色彩和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一种冷肃、猛烈的思想撞击力从而使这部作品激荡着巨大的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思想力量”[8]。还有的批评者既指出这种“将生活的激流以倾诉的方式展示”的处理方式“罕见”,又认为它“缺乏让事实获得自身力量的处理的大度”,本质上“只是一种自言自语式的个人内沟通”,与时代形不成真正的对话关系[9]。
小说的确大量采用随笔的体式,这是因为“思想随笔”恰恰是张炜一直实践不曾间断的一种文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凭恃散文和随笔文体的自由,他切直深沉又坦荡洒脱地进入受限于小说和诗歌文体美学的严饬而不得或不便深入的领地。同时,他又格外注重思想性对散文的统摄,给散文自由的形式筑起一道道精神的堤坝,让散文同样具备“建设人的思想”的骨力。在张炜那里,散文既是其小说最好的声援和阐释,也是比小说更直接更朴素地肉搏时代的利器。《柏慧》的“一气呵成”,恰恰得益于他的积累。
很多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关于“二张”和“二王”之争的文章都分外看重1993年。从这年年初开始,一系列的事件都像是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登场的着意准备:《读书》第 1 期发表了王蒙的《躲避崇高》;1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新交易大厅正式启用,李鹏总理视察并题词:“努力办好深圳证券交易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以《灵与肉》《绿化树》等蜚声文坛的张贤亮,创办了“华夏西部影城有限公司”……同样是在1月,张炜的《融入野地》发表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融入野地》本是张炜为《九月寓言》写成的“代后记”,《上海文学》的编者将它放在头条发表,并在《编者的话》中高度评价其意义:“这篇作品不仅仅是张炜的内心独白,而且可以堪称是张炜那一代‘知青作家’的一个‘精神总结’。”《融入野地》文中的“我”是一个大地心音的倾听者和记录者,一路奔逃开城市,由故地而野地进而成长为野地上的一棵树,在与自然的彼此关情中克服了生命本然的孤独。“野地”和“树”是被“我”这个不合众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所照亮和赋意的,也即文中所谓的由“知”至“灵”。如《上海文学》的编者所言:“张炜在这篇近作中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既充满理想情怀,又脚踏实地,坚持其精神劳作的我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我们可以将这篇文字看作小说,也可以看成是散文,是议论,是诗,是一种超越文体界限的文体。”而这也正是《柏慧》所用的文体。试看:
……这越来越像是一场守望,面对一片苍茫。葡萄园是一座孤岛般美丽的凸起,是大陆上最后一片绿洲。你会反驳“最后”这个说法,是的,但我相信这样的葡萄园不会再多出一片了。为此我既自豪又悲凉,为了我特别的守望,我母亲般的平原。
我必须寸步不移守住平原。因为它通向高原。故地之路是唯一的路,也是永恒的路。我多么有幸地踏上了这条路啊。我永远也不会退却。我的伤口在慢慢复原,渐渐已能站立。我又看到了蓬蓬长起的绿草……
我沿了一条小路走去。小路上脚印稀罕,不闻人语,它直通故地。谁没有故地?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绺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
以上三段可以组接成一篇小文,但其实它们原本并非连贯的,第一段和第三段分别出自《柏慧》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中间一段则选自《融入野地》。这充分说明,《柏慧》与《融入野地》在语感语意以及精神题旨上的贯通,或者毋宁说,《柏慧》就是《融入野地》的一个长篇版本,是同一名战士更赤诚和焦灼的“心灵的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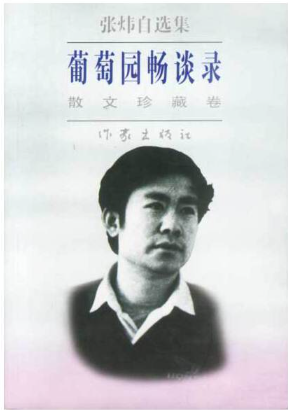
张炜:《葡萄园畅谈录》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柏慧》的缘起还可以再往前推。1996年2月,作家出版社在“张炜自选集”系列中首次推出了张炜的长篇创作谈《葡萄园畅谈录》,内中收录了他写于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间关于文学、文化、自然、人生和时代的数百篇札记,读者可以从中清楚看到朝向《柏慧》的“精神的思缕与火种”。比如,在第二篇,他就写到无边无际的葡萄园正在被开发区吞噬,“浅薄无知和贪婪的心性”制造了“虚假的繁荣”和“真正的贫困”,表示“对待这种耻辱,人要有义愤、有表示,心中无愧……”——那个与柏慧和老胡师作深挚长谈的男人不是在六年前就已经站在了海滨的葡萄园边,锁紧了眉头吗?我们再举一例,萧夏林主编的《抵抗投降书系》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直接产物,影响不小,其中《张炜卷·忧愤的归途》前半部分所选张炜的散文写于1980年代的亦不在少数,最早的一篇《一辈子的寻找》作于1985年。这也充分说明,张炜站在“大地梦想的中央,以不宽容、不容忍、不退却、不背叛、不投降、仇恨和永远战斗”[10]去回答时代之问的姿态并非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1993-1995年才形成的,而是他出道文坛后素来的站位,《融入野地》和《柏慧》所提出的“寻找一个去处”和“落定”的问题,也是张炜散文甚至张炜文学世界终极的命题。
值得注意的还有,王晓明和自己的学生在《旷野上的废墟》中所指摘的“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诸多表征,如作家的商业投机、先锋文学的技术偏失等与张炜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明确要“拒绝”和“抵抗”的时代病相几乎一致,《葡萄园畅谈录》就记录了大量关于类似“危机”的思索。不妨这样说吧,如果《九月寓言》《柏慧》和写于此时的一批散文是喷涌四射的岩浆,那也是因为它们早已作为地火在暗处灼热的蓄势了,《柏慧》是一部张炜注定要写出且早经酝酿的书,只不过热闹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像一枚引信,让他素来的思考和忧虑获得了集中倾吐的机会。也因此,张炜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被发掘和标举,被阐释乃至误读,几乎是必然的,他不是最直接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但是最早最忧虑的预警者。
“天生浪漫者”的保守与激进
“道德理想主义”,这个短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等同于“二张”,而两者同义的关系正是被“人文精神大讨论”所建立的。如何评价张炜在《柏慧》等作中所体现的忧愤的“道德理想”,批评界聚讼纷纭,最有意味的则是对这一概念“保守”或“激进”的不同定性。王岳川在1990年代末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把张炜所实践的“道德理想主义”归于文化激进主义的范畴,认为:“这种尖锐抗争的精神,秉持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 即强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坚持道德化、理想化的倾向,固守时代的正面精神,遵从崇高, 讲求人的尊严,要将被世俗社会放逐的神圣感重新寻找回来,而赋予时代一种人文色彩浓郁的精神性乌托邦。”[11]不过,更多的批评者如贺仲明、颜敏、谢有顺等则认为《柏慧》里的“农业理想”、与改革发展的“逆反趋势”、对工具理性的质疑等等体现的是张炜从1980年代启蒙立场的回撤和鲜明的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12]。
张炜自己的创作似乎也在把自己锚定在了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形象上。他有一篇文章写于1988年,题目就叫《缺少保守主义》,表达了对做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写作者的诚笃,内中谈到:“能够坚定地、一贯地固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确是陈旧的或至少看上去是陈旧的——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13] 请注意1988年这个年份,1990年代思想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通常被追溯到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张炜此文受到余英时的启发。但这个年份的巧合提醒我们,张炜的思考往往与时代主潮形成错位的对话关系。在整个1980年代,张炜的创作始终与热点和流行的话题保持着距离,所以他也很难被标签化地固定到某一文学思潮和概念之下。以《古船》而论,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反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有人视之为改革文学的扛鼎之作,还有一些讨论则将其放入寻根文学或新历史主义的框架中加以研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爆发,置身风暴眼中的张炜其实一直未变,但却于此时暗合了王晓明等对“人文精神”的召唤,从而被塑造成“抵抗投降”的旗手,并最终在评论界形成前述与“道德理想主义”胶合在一起的评价定势。而对于张炜激进或保守的不同论断,与论者对“道德”和“理想”的侧重诠释有关,即保守论者多取“道德”理解,着重对张炜泛道德主义的评价;激进论者着眼点则在“理想”之乌托邦冲动和“绝不宽容”的气概,以及对失范的机器文明的愤怒诅咒上。
事实上,在张炜那里,“道德”与“理想”不是泾渭分明的,无论被解读为保守还是激进,张炜所坚持的都是一种精神性的价值立场,而这种价值立场的形成与他对浪漫主义精神的珍视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在其时围绕《柏慧》的诸多讨论中,并未获得展开。1984年,在《讨论“浪漫”》一文中,他认为浪漫主义的根本在于“一个人生命的性质:激情、想象、才情……一切都是由它决定的”,“这差不多等于说:这个人天生是‘浪漫’的”[14]。二十年后,在《冬夜笔记》中《流浪的知识分子》这一节中,张炜又这样写到:“我们时时都在幻想,期望在今天呼唤出一种真正而非虚假的浪漫主义。一个时代没有这样的浪漫,,就没有领衔的艺术和思想。……一个时代缺乏真正的生命的激情,就不会有真正的浪漫主义……要知道一个人的激情不与顽强的坚持结合在一起,不能焕发出生命灿烂的诗性。”[15]紧随这一节的如下几节标题分别为《“现代性”质疑》《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的独特性》等,“人文”“知识分子”“精神”这些词密集出现,写作时间上虽已经与“大讨论”拉开了一段距离,但张炜态度一仍其旧。同时,这提醒我们,张炜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是本源性的,浪漫主义是他的忧患诗性和批判力的发源,其保守或激进也需要在浪漫主义的框架里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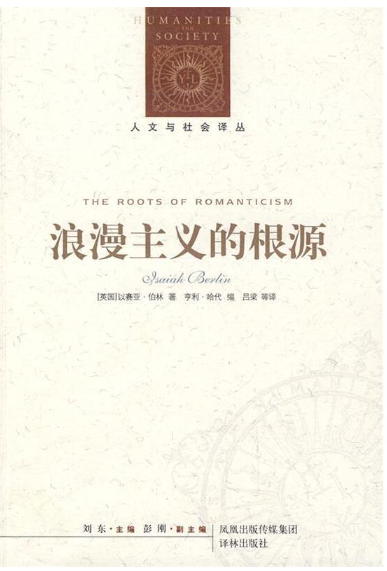
[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
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张炜一直很推重的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认为,浪漫主义才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和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重大运动不同”,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成功地使人的一些价值观产生了深刻转变”[16]。柏林的结论是:“浪漫主义给予我们艺术自由的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十八世纪曾盛行的、过度理性和极端科学主义的分析者今天仍在阐述的那些过于简单的观点,无法用来解释艺术家个人或人类的全部。浪漫主义还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观念,对人类事务做出一个统一性回答很可能是毁灭性的……”[17]张炜自80年代以来诸多关于创作的思考与柏林的结论是不谋而合的,尤其体现于他对技术主义的批判和对作家精神主体性的坚守,像《缺少保守主义者》和《讨论“浪漫”》等文,其重心即在作家对纯粹、清洁、质朴、“拒绝投机”的写作立场的确认,而《柏慧》更是可以看作柏林所定义的浪漫主义的典型文本,内蕴着“进步”与“反动”的二重性。
具体来说,就《柏慧》所体现的保守性来看,与1990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如国学热、回归学术等其实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与被允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作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等也并不相同。张炜确实谈到过对本土人文传统的激活,也有不少评论者分析过其作品所体现的儒家思想或道家智慧,但就《柏慧》而言,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并不主要来自传统。小说在人性的美与丑、纯洁与污浊、忠贞与虚伪、坚守与放弃间划出分明的界限,并以对自然的彻底回归独对世俗的理性谵妄。这种“二元对立”被不少批评者认为是对复杂现实生活的简化,但张炜却坚持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是去除“时代的油皮”“最好的办法,也是必由之路”,并将之视为写作的“底线”和“立场”[18],其背后即隐含着浪漫主义对善和美要屈从于功利的抗拒,“浪漫主义力图想治愈世界的荒凉,这是二元论的痛苦认识”[19]。张炜笔下的故乡、海滨平原、葡萄园、野地,既是他成长中留下深刻生命印记的“实地”,同时又无限向大地敞开,彰显着幽深玄远的灵性,它们不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或生活形态,而是一种价值形态”[20],张炜的流浪和回撤也并非要拥抱前现代古老的生产方式,或单纯颂赞农业文明,而是要在更澄阔的境界里让自然的“崇高”归位。
就其激进性而言,构成浪漫主义核心要素本来就包括自由无羁的意志和生命的激情,就如张炜在八九十年代的散文中大量使用诸如“信仰”“牺牲”“殉道”这样的语汇,甚至他有篇散文名字就叫《艺术是战斗》,他倔强地要在一个世俗时代的背景中凸显“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个体”。与这些“战斗”的语汇匹配的是“心灵”“灵魂”“诗”和“知识分子”,《柏慧》里,主人公曾这样说到:“真正的知识象真理一样, 它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中心。它的中心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只有心灵才是它的居所。……真正的知识分化为诗,它们是一致的、 合二为一的。一切脱离了诗性的知,或脱离了知性的诗,都会程度不同地冒出一丝浅薄气和虚假气”。这与柏林定义的浪漫主义的两个核心观念——其一,“不屈的意志”,即“人们所要获得的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而是价值的创造”;其二,“世上并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不存在一个你必须适应的模式”[21] ——不是正相符吗?
汪晖有段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思考,常被引用:“人文主义者关心人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而主要不是生产方式的问题。对于这种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呼吁,我的问题不是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而是为什么是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例如,对于整个社会过程的重要变动,为什么不是从生产方式、资本的活动、全球性市场,以及所有这些重要社会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关系来着手分析,而是把人文精神的失落视为社会变动的原因或结果?”[22]《柏慧》的主人公和张炜本人也面临这个问题。结合前文来看,张炜是从一个本源性的浪漫主义作家的良知出发,通过对“诗与真”的坚持一步步链接到人文精神上的,并形成了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途径”的思路,他的“价值立场”与《柏慧》的批评者所持的“历史立场”其实并没有真正在一个层面上构成对话。不妨把围绕《柏慧》的争议稍作一点延伸,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不少曾经被认为是开倒车的人物,如“五四”时期的杜亚泉、学衡派,当人们跳开时代回看却发现,他们的探求和思索往往代表的是对工具万能论予以反省与批判的另一现代性路径,也是与主导性的历史行为和历史观念相对峙的必不可少的制衡力量。这才是《柏慧》的“保守”和“激进”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就像一位学者反思的,“人文精神”的发动固然有其空疏和乌托邦的一面,但那么多年过去了,在越发强调知识细分和人文专业化的当下,“为什么我们丧失了从精神、从价值和道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能力?为什么关于生存意义的探索在近二十年几近于无?”[23]
一点补充:在两种“恶”的背后
近十年来学界对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那就是“讨论”与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的关系,尤其是与上世纪50-70年代的联系。如程光炜的《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即从当时王蒙等的观点出发,认为“由于当时人文精神倡导者只是在人文学科危机的相关范畴里面向90年代的问题,而没有在‘十七年’与‘90年代’之间建立一个关联性的逻辑结构,没有意识到90年代物质欲望的突然膨胀恰恰是‘十七年’的严重物质匮乏造成的这样一个中国问题,这就使这场讨论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必要的历史感”[24]。杨庆祥的《寻找历史的缝隙——关于 “人文精神讨论”的述评与思考》认为,王晓明发动“大讨论”有一个“40年代+80年代”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里,‘人文精神的失落’实际上被理解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失落,文学的危机也被理解为知识分子放弃‘独立人格’和 ‘主体地位’的危机”,而“十七年”被这个参照系有意无意地删除了[25]。

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不过,王晓明其实并未忽略构成其重要成长背景的50-70年代,在1995年2月为论文集《刺丛里的求索》所写的序言中,他从自己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里“长大成人”谈起,如何拥抱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如何又被80年代晚期的社会变化吹得“懵头转向”,又如何在对理想“幻觉的历史渊源”和“自身意识结构的深层缺陷”反思的基础上,以终极价值和重建自我信仰为诉求,发动并参与“人文精神”讨论[26]。薛毅对王晓明的这段自白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解读,他指出,要充分考虑到6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和社会运动对当时青年一代的“铸造力”,王晓明把“文革”的影响概括为“既渴望理想,又缺乏理想”,是指“理想只在形式上存在而没有具体内容”,王晓明的这种心灵结构普遍地存在于知青一代作家中,然而“具体的理想形态之间的替换,并不容易,尤其当一个人与某种理想形态之间形成了血肉联系,……重新获取新的理想,使之与自己血肉相连,同样也需要艰难的过程”[27]。张炜出生于1956年,只比王晓明小一岁,属于同一代人,当然也有相似的心灵结构。在《家族》的序言中,他也曾着意引用过小说中人物这样一段话:“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和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28] 表达的不正是同样的感慨么?
不同的是,王晓明在“人文精神讨论”里将矛头指向1980年代中期以来理想涣散、精神颓堕的文化和文学,隐藏了50-70年代的思想前史,张炜的的忧思不但指向市场经济的时代潮流,也指向此前被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反复叙事过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尊严被践踏的“极左”年代——从“秋天”系列开始,他就总是“在历史长河中去叙述权贵的来龙去脉”[29]。在《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中,张炜抨击了两个年代两种现象:“在那个横行无忌的年代里,不少人在用一支笔去迎合。在如今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又有不少人在用一支笔去变卖。”[30]在《柏慧》里,恶人有两种:一种是瓷眼和柏老这种带有“极左”年代的遗风,以权势凌驾学术,并对真正的知识分子从精神到肉体上进行残害的人;一种是主人公曾经供职的杂志社为了销路而取悦世俗的柳萌等同事,以及对葡萄园虎视眈眈并试图侵犯的“鹰眼”之流。而且《柏慧》的抒情主人公用了相当篇幅追忆自己的家族史,对革命有功的祖父被杀,父亲被审查、监管,自己因为出身问题在地质学院备受刁难;追忆了山地老师的潦草的死,口吃老教授和儿媳在运动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惨状……在张炜看来,慑于权势暴力的背叛和拜倒在资本下的背叛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些“基本的、并不复杂的检验”,然而卑贱却真是成了卑贱者的通行证,03所的“事实就是这么严重,就是在流血,而且这血直到今天还在流,流个不停……”由此,《柏慧》书写了两次流浪:第一次流浪,是父亲被监管迫害时,母亲为了让“我”免于家庭的连累而想另找一户人家收养“我”,“我”出于恐惧逃往山地,开始流浪;第二次则是“我”经历了地质学院、03所、编辑部,见识了污浊和虚伪后,逃回海滨的平原,在葡萄园里建起“最后一片绿洲”。每一次流浪,民间世界都以其素朴、仁慈和率性疗愈“我”,书中的四哥、响铃、鼓额仿佛从《九月寓言》中奔跑出来的人物,全都带着浑然的民间气息。在《柏慧》中,民间既是与庙堂相对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寄居地,也是让真正的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获得正义、敏感和勇气的支撑,同时它还链接起知识分子的过往之罪与时代之殇,并让叙事者见证了大地的苦难和韧性,坚贞了他站在清洁的穷人一方的选择——虽然,这个民间与1990年代批评界讨论的民间概念并不一致。
如此说来,被良知催逼产生的《柏慧》其实依然包含了张炜此前作品中都有的诸多的历史反思。如前所论,张炜的抒情、议论和批判都是基于“价值立场”,与坚持历史理性立场的批评者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柏慧》对柏老和瓷眼等人罪行的揭露等却让小说具备了另一种历史的分量,提供了关联90年代思想状况和50-70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特别角度,只是这一点在其时的“讨论”中也未被深入论及。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注 释
[1]张炜:《柏慧》,《张炜文集》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后文出自《柏慧》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另注出。
[2]张炜:《兼谈》,《张炜文集》第32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
[3]昌切、刘继明:《<柏慧>与当下精神状况》,《山花》1995年第11期。
[4]张炜:《心中的交响——与编者谈<家族>》,《张炜文集》第30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149页。
[5]宫达:《“一个人爱艺术多么美好”——张炜印象记》,《文学世界》1998年第1期。
[6]孙绍振:《<柏慧>:不成立的写作》,《小说评论》1995年第6期。
[7]吴义勤:《拷问灵魂之作——评张炜的长篇新作<柏慧>》,《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8]李建军:《坚定地守望最后的家园——评张炜的<柏慧>》,《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
[9]徐德明:《<柏慧>: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当代文坛》1996年第2期。
[10]萧夏林:《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写在<抵抗投降书系>的前面》,《抵抗投降书系·张炜卷:忧愤的归途》,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11]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2]参见谢有顺:《大地乌托邦的守望者——从<柏慧>看张炜的艺术理想》,《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贺仲明:《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80年代精神之一种嬗变——以张炜为例》,《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颜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3]张炜:《缺少保守主义》,《张炜文集》第27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页。
[14]张炜:《讨论“浪漫”》,《张炜文集》第27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15]张炜:《冬夜笔记》,《张炜文集》第37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
[16][17][21][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144页、120页。
[18]张炜:《从“辞语的冰”到“二元的皮”——长篇文体小记》,《张炜文集》第35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页。
[19]参见[美]维塞尔:《马克思主义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20]王学谦、张福贵:《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北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2]汪晖:《中国的人文话语》,《死活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23][27][29]薛毅:《人文精神的讨论》,《都市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
[24]程光炜:《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文艺研究》2013 年第 2 期。
[25]杨庆祥:《寻找历史的缝隙——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述评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26]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28]张炜:《家族》,《张炜文集》第9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30]张炜:《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张炜文集》(第29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