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晚,中国当代文坛实力派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做客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直播间。二人以“让我们邂逅文学之美”为主题,展开了精彩对谈。
俞敏洪分享了自己阅读张炜作品的感受与体验,从第一次结识张炜作品《我的原野盛宴》开始,到最新出版的《唐代五诗人》,二人一起回顾了张炜写作生涯不同阶段的作品以及创作历程,与读者共享文学之美。

01
俞敏洪谈《我的原野盛宴》:
张炜作品的营养源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俞敏洪:张炜老师,你的书我读了不少。读你的书主要开始于《我的原野盛宴》,这书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我十八岁之前一直在农村长大,尽管我的童年和你的童年在大海边、树林的环境不一样,但是你的书又把我带回到农村时期曾经的岁月。我从你的每一本书,包括小说、散文、儿童作品中,都能读到胶东半岛的生活对你个人成长的影响。而且我觉得在书中任何地方都透露出胶东半岛齐文化的气息。古时代曾把山东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鲁国,一是齐国,你作为山东人,山东文化对你的成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张炜:显而易见,您虽然是南方人,但对齐鲁文化非常熟悉。齐国和鲁国相邻,平常我们讲齐鲁文化,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我出生的地方是胶东半岛,黄河以东的地方属于古齐国,我们受鲁文化影响都很大,这个我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齐文化的基因还是蛮强大的,从而形成我的创作风格与个人气质。

俞敏洪:读《我的原野盛宴》,对你描写的树林中的环境感觉那里如同桃花源一般。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我想,这跟你的童年是密切相关的。你的童年时期是不是就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海边的树林中呢?
张炜:对。《我的原野盛宴》是一个非虚构,所以必须写得真实,有点自传的味道。在写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对我的成长,可能在我所有的作品里这是最用力的一部。
俞敏洪:因为童年时期一般对自然环境的敏感性要远远大于对社会环境的敏感性,换言之,社会环境对童年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直接作用。
我对你书中所描述的茅屋非常感兴趣,你生长的茅屋真的是独立于村庄的存在吗?

张炜:是的,和书上描写的完全一样。那里没有人烟,海边只有一个渔码头。
俞敏洪:从你住的茅屋到海边有多远的距离?
张炜:7华里左右。
俞敏洪:小时候住在这么一个独立的茅屋中间,除了书中写的跟动植物为朋友以外,你个人在那种环境中生活会觉得孤单吗?
张炜:孤单是有的,当跟社会方面的交往少了以后,就会变得内向。但是另一方面,跟植物和动物的交流就会增加。
俞敏洪:在书中,对于动植物的名称是非常熟悉,我稍微算了一下,在《我的原野盛宴》中,至少涉及几百种动物和植物。在此,我认真推荐《我的原野盛宴》,这部描写童年和外祖母在一起生活、成长以及与大自然、动植物和谐相处的纪实性作品,这本书太值得读了!

我在《我的原野盛宴》中读到,你的外祖母和母亲对你十分重要。你和外祖母住在茅屋里面,外祖母对你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外祖母,包括母亲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以及对你未来的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吗?
张炜:外祖母给我奠定了人生的基础,她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亲人之一。我的文字里面也出现了大量外祖母,有的时候虚构作品里面也会有她的影子,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了,待人接物,生活中的一些规矩,都来自外祖母的教育与影响。
俞敏洪:我的外祖母、母亲对我的影响也非常重要,所以读《我的原野盛宴》特别有感触。我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小时候跟大自然接触比较密切,长大以后对于生命和大自然的热爱,以及生命的宽度,一定会更加广阔。这种热爱在你的每本书中都能读到,包括《斑斓志》《唐代五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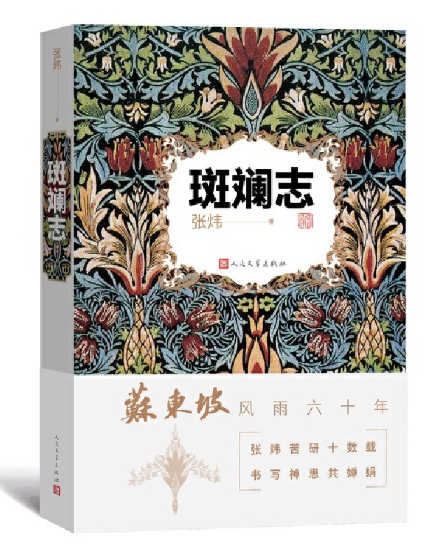
张炜:我想起你的《在岁月中远行》这,“远行”两个字很打动我。由于我很早离开了家,没有一直在父母身边,在胶东半岛一直转悠到考大学,“远行”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吸引力。《你在高原》中写了两段行走,一个是少年时代,一个是青年时代。
俞敏洪:通过阅读走向写作,你的文笔非常优美,在此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你怎么走向写作这条路的,什么机缘让你坚持几十年写作的?
第二,你上的学校现在叫太阳成集团,当时是师范大专学校,初高中时期并没有受过真正的严格的文字训练,但是你现在驾驭文字的能力,包括研究古代诗人的作品、讲课的能力,以及写小说、写散文,包括写诗的能力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张炜:看了我的《我的原野盛宴》,你注意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自然对我的培育,再一个是孤独和阅读,尤其是深入的阅读。太阳成集团为新改校名,这所学校其实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学校教育是重要的,但无论如何,对于从事学术和艺术而言,那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是太初级太单薄了。这需要终身、更复杂的学习,是这样的过程。
俞敏洪谈《唐代五诗人》:
真实地把诗人生命和思想的多面展示了出来
俞敏洪:另外再说说你创作的另一方面。我读了你写苏东坡的《斑斓志》,特别喜欢,觉得关于苏东坡怎么讲得这么好!后来又读了《唐代五诗人》,感觉你对这五位诗人的成长环境、性格、境遇,以及对他们的人生格局、性格与命运关系的分析,挺有感触。你写了这么多古典的诗人,我发现你对每个诗人的分析有一个特点:尽可能真实地把他们的生命和思想的两面或者多面都展示出来。你的作品分析了李白、杜甫,我们印象里李白、杜甫都是完美的形象,一位是诗圣,一位是诗仙,你提到他们为了能够在京城当官去拜访达官贵人,做出一些求爷爷拜奶奶的事情。关于陶渊明,我们一直认为陶渊明就是世外桃源,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他在追求与世俗共鸣和退到田园生活中间也有着各种挣扎。你的分析让我们实实在在看到,心中崇敬的诗人他们真实的生命状态。我看完这些,一点没有觉得贬损他们,反而让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饱满了。你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研究这些诗人?
张炜:我个人觉得,诗学研究最终还要回到生命本身。艺术是生命的产物,对一个人、对他的生命旅程没有搞清楚,也很难懂得他的艺术。关于陶渊明、李白等古代诗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他们简单化、符号化和概念化。
02
俞敏洪谈《唐代五诗人》:
真实地把诗人生命和思想的多面展示了出来
俞敏洪:另外再说说你创作的另一方面。我读了你写苏东坡的《斑斓志》,特别喜欢,觉得关于苏东坡怎么讲得这么好!后来又读了《唐代五诗人》,感觉你对这五位诗人的成长环境、性格、境遇,以及对他们的人生格局、性格与命运关系的分析,挺有感触。你写了这么多古典的诗人,我发现你对每个诗人的分析有一个特点:尽可能真实地把他们的生命和思想的两面或者多面都展示出来。你的作品分析了李白、杜甫,我们印象里李白、杜甫都是完美的形象,一位是诗圣,一位是诗仙,你提到他们为了能够在京城当官去拜访达官贵人,做出一些求爷爷拜奶奶的事情。关于陶渊明,我们一直认为陶渊明就是世外桃源,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他在追求与世俗共鸣和退到田园生活中间也有着各种挣扎。你的分析让我们实实在在看到,心中崇敬的诗人他们真实的生命状态。我看完这些,一点没有觉得贬损他们,反而让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饱满了。你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研究这些诗人?
张炜:我个人觉得,诗学研究最终还要回到生命本身。艺术是生命的产物,对一个人、对他的生命旅程没有搞清楚,也很难懂得他的艺术。关于陶渊明、李白等古代诗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他们简单化、符号化和概念化。

俞敏洪:有人说,古代的诗歌是轻人和年纪大的都能写,杜甫年纪那么大还写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个时候离他的去世都很近了,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现在的诗歌大家都觉得好像只能年轻人写,年纪大的人写现代诗歌好像感觉不对。你同意现在诗歌只能年轻人写的观点吗?
张炜:我觉得肯定不是的,和一切文学体裁一样,杰作有可能出自青年,也有可能出自老年。莱蒙托夫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写了那么多好诗。兰波也是二十多岁写出《奥菲莉娅》。的确有上年纪才写出好诗的,歌德晚年才完成《浮士德》,哈代也是老年才成为大诗人,所以说,有人认为年轻人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不一定对。诗是生命的产物,而青春仅仅是生命的一个阶段。
03
张炜忆《古船》:
多么渴望拥有那时的纯粹、热情和勇气
俞敏洪:《古船》是你小说中我读得最上心的一本,读完以后很有感悟,刚好有农村小镇的场景,又是几个家族。我小时候就在农村小镇几个家族之间长大,我母亲是我们村上第一个承包生产大队小工厂的,所以隋家和赵家争夺的场景跟我小时候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历很相像,我读得很有感悟。写这部小说是因为你刚好生活在这个小镇看到这种场景?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

张炜:《古船》是我二十七岁开始写的,二十八岁完稿,出版过程经历了很多挫折,出版时已经30岁了。我当时不觉得自己年轻,现在看那时候太年轻了,未免幼稚。生命是有奥秘的,二十多岁拥有的纯粹和勇气、冲决力,有时候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丧失了一部分,但可能获得了另一部分能力。比如写《九月寓言》的时候,我写不出《古船》。现在我是多么渴望再有《古船》的那种纯粹、热情和勇气,又有《九月寓言》那种华丽,成熟与饱满。但一个人后来的作品不能取代原来,无论现在写得多么好。我现在回忆写《古船》的感觉,那种心弦紧绷的状态,整个人在跟自我搏斗一样,一生就写这样一本书,当时觉得也值了。
俞敏洪:写完《古船》以后会想到自己还会写那么多长篇小说吗?
张炜:没有想到。我当时想,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写出一部《古船》,这就死而无憾了。我那时候整个人完全沉浸、融化在那个世界里面了。但是当生命继续前进,继续生活,又会有新的激越,比如产生了写《九月寓言》这种强烈的欲望。

到目前为止,专业界认为《九月寓言》是我最好的作品,将来也不一定超过。三十岁左右写出《古船》和《九月寓言》,如果只跟自己比,这像是两道大坎,我后半生需要用全部力量去超越这样的小说,我要汲取、积攒极大的力量。所以,人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想超越他人,年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但是后来会慢慢发现,古今中外所有作家的作品,可以看成一体,它们恍若浑然庞大的“民间文学”,是难以超越的,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比巨大,这种庞大性决定了其是不可超越的。就每个人来说,他每一阶段的作品也难以超越。因为生活经历不一样,二十岁写的东西怎么让六十多岁、八十多岁去超越?八九十岁创造出来的东西,又是另外一种成色。每一段的生命河流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像《独药师》,这是近六十岁的作品,给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生命快感。
《在岁月中远行》这本书,“远行”这两个字,可能是指精神的远行。
俞敏洪:那是我一本小小的游记,在国内国外旅游的记录。
张炜:我想读您的自传,哪本书更接近您的传记?
俞敏洪:《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生活中谁都会产生厌倦的情绪,您是怎么克服生命中的厌倦的?并且到了六十多岁依然有这么大的热情在写作,而且还出版了不少质量很高的新书,这是怎么做到的?
张炜:重复一种劳动、重复一种事物虽有成就感,也会产生疲惫感。厌倦和困倦是必然的。但是当遇到倦怠的时候,就要寻找战胜的方法,这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更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过分强调结果,就很少去考虑过程了。比如写每一本书,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这部书写好了、成功了,有影响,固然是件好事情,但是最大的快乐还是在营造这部书的整个过程中。战胜厌倦的过程更有意义。以后还会有厌倦,但是一定还要重建、重新出发。有这样一种能力和精神状态就好,但愿我能够保持下去。我是看重过程的。
俞敏洪:有人说两个人之间其实最美好的感情最后也会走向厌倦。我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林黛玉没死,跟贾宝玉结婚了,他们会走向什么结局?
张炜:贾宝玉和林黛玉写的是二人开始相处的那个过程,没有讲后面的结局。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品质很高的人,他们会重建的。
俞敏洪:最后一个问题,您自己生命中有过与人的关系走向厌倦,最后又重建成功的案例吗?
张炜:许多时候,争论不如告别。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对方。但也有很多别的案例,比如有很多好朋友,交往长了,不停地重复一种语言和观点,还有由于观念的不和,最后不能作为朋友了。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我们全在新的方向上达成一致,加强了、提高了,又成为好朋友。几十年是多么不容易!厌倦、告别、重建、再出发,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朋友之间也好,事业也好,一言不合分道扬镳,急于告别和分手并不好。要尽量寻找重建。
俞敏洪:现在还有那么多网友在陪伴这场对谈,您对网友们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张炜:今晚的对谈很高兴,和俞先生的对话聊了很多很朴实的话题,最重要的是读书方面。我希望我们的读者去多读相对寂寞、相对有难度的书,寻找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艺术。网络时代,读书是很奢侈的事情,大家都很忙,一部手机就把我们牵得团团转。在这种情况下,要读就读那些,若不读一生都要后悔的书、读特别好的书。
俞敏洪:张炜老师,我在东方甄选的平台等您,谢谢!
